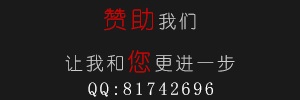赌场无间道
2019-07-10 15:48:00
次阅读
稿源:故事大全
在麻坛上,最低级的作弊者,称为赖子;技术高的,称为老千;技术更高一点的,称为大老千;作弊达到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之人,便会被大家称为“麻仙”……
1. 夜救
赵清源喜欢打麻将,也爱作弊,只是作弊的手法拙劣,无非也就是偷牌换张,装作东西掉地下,弯腰去捡,趁机偷看别人手里的牌等等,经常被人发现。所以,像他这种人,只能算是个赖子。
这天晚上,赵清源和往常一样,又在家附近的麻将馆里输了个口袋溜光,正垂头丧气地往家走。突然,他发现前面地上有一团黑影,赶紧走近一看,原来有个人脸朝下躺在地上。
这个人莫非是喝醉了酒?赵清源一边想着,一边伸手去翻这个人的身子。这一翻开身子,把赵清源吓了一大跳。这是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的老人,脸色乌紫,嘴边还挂着一长串白沫。
赵清源虽然嗜赌如命,但心地还算善良。他当即背起昏迷着的老人,一溜小跑地将老人送进了医院。
送进医院得交医疗费,可赵清源翻遍了老人的口袋,除了找到一包香烟、一把零钱和两张银行卡,便别无他物了。联系不上老人的家属,老人又昏迷不醒,银行卡里的钱取不出来,最后实在没招了,赵清源只好给妻子江晓蕾打电话,让她把明天进货用的三千块钱送来救急。
江晓蕾这人,对丈夫打麻将管不住,但良心特好,听了赵清源的诉说,便匆匆起床,奔向了医院。
十多分钟后,江晓蕾替老人交上住院费,老人推进了急救室。
抢救手术一直进行到凌晨,一位大夫从急救室里出来,说:“病人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患的是脑溢血,要是再晚抢救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刚进行完手术,病人过些时候才能清醒。”
赵清源两口子折腾了大半夜,到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家开了一间烟酒店,江晓蕾先要去开门做生意了,留下赵清源一个人守在医院里。这时,护士又来催促赵清源去交医疗费。
赵清源以为护士搞错了,理直气壮地说:“昨天晚上不是刚交了三千块吗?”
护士说:“用完了,抢救时用的全是好药,那三千块早就没了,你得再交三千块。”
“什么?还得交三千?”赵清源吃了一惊,说,“是这样的,护士小姐,这老头儿跟我非亲非故,我都已经替他交三千了,剩下的医疗费,你们能不能等他醒了,让他来交?”
护士冷冰冰地说:“我们不管,如果你不替他交钱,我们就停药。”
赵清源有些火了:“你们医院怎么这样呢?这不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吗?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
护士也提高了嗓门,说:“我们怎么啦?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病人不交钱,我们总不能拿自己的工资往里垫呀!”
两个人正争执着,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痛苦地哼了一声,醒了。
赵清源赶紧说道:“哎哟,我的老爷子!你可总算醒了,人家正要钱呢,卡里有钱没,快交出来。”
老人刚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是盯着赵清源看。
看到老人没明白什么意思,赵清源便从头到尾将昨晚发生的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
老人听后,说:“小伙子,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兜里有银行卡,你帮我拿过来好吗?”
赵清源帮老人找出银行卡,老人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抽出一张交给赵清源,说:“小伙子你再帮个忙,这卡里有一万块钱,我把密码告诉你,你去帮我取出来,行不行?”
赵清源爽快地答应了。
中午,江晓蕾到医院送饭。在服侍老人吃饭的时候,江晓蕾得知,老人孤苦伶仃,没有什么亲人,昨晚睡到半夜,觉得胸口发闷,便想出来散散步,谁知,刚走了一小段路,便摔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听了老人的话,江晓蕾动了恻隐之心,便劝慰老人说:“大爷您放心养病,我们两口子也不太忙,可以轮流过来照顾您。”
后来,赵清源两口子又得知,这位老人姓萧,名叫萧环山,老家在东北,年轻时来到了南方,便一直没有回过老家。萧大爷年轻时结过一次婚,可后来妻子因病去世,萧大爷没有再续弦,孤身一人度过了半生。
老人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赵清源夫妇耐心地侍候了老人一个多月。后来,老人身体康复了。办理完出院手续,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老人突然停下脚步,对赵清源夫妇说:“小赵、小江,你俩跟我非亲非故,我不能白白让你俩侍候我这个糟老头子一个多月,我得报答你们。”
赵清源一听萧大爷的话,怀里像揣了只兔子似的怦怦乱跳。他想,萧大爷一定是要给自己些钱,不知能给多少呢?
“大爷,千万别说这种客气话,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我们可不是冲着这个才照顾您的。”江晓蕾接口说,“咱们能认识,这就叫缘分,我们两口子不缺钱花,您的钱留着养老用吧!”
赵清源见妻子这样说了,尽管心里不情愿,但也只好顺着妻子的话说:“是啊,萧大爷,我们不缺钱,不需要您的报答。”
“谁说要给你们钱了?”萧环山笑着说,“赠人千金不如教人一技,千金总有花光的时候,可是只要有一技在手,便可以一生一世吃喝不愁。”
赵清源一听老人不是要给自己钱,顿时大失所望。
不过,江晓蕾倒是来了精神,说:“那敢情好,我们家清源呀整天游手好闲,我正巴不得让他学门技术,好干点正经事儿呢!”
萧环山笑了:“我这门技术呀,说起来还只有游手好闲的人才能学得会。”
赵清源被萧环山的话给逗乐了:“什么技术?”
萧环山笑眯眯地说:“打麻将。”
“大爷您开什么玩笑,现在我都管不了他了,天天打麻将,不把钱输光都不肯回家,”江晓蕾急了,“他学啥都行,就是不能学打麻将。”
赵清源边笑边说:“大爷真是会开玩笑,打麻将还用得着学?一看就会的玩意儿。”
“我没有开玩笑,”萧环山很认真地说,“你打麻将总是输,那是因为你不会打麻将,你要真正学会了,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赵清源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试探着问道:“莫非……莫非您老人家就是传说中的麻仙?”
萧环山笑而不答。
2. 学艺
赵清源开始拜师学艺了。
江晓蕾虽然反对,但架不住赵清源的软磨硬泡,再加上听萧环山把打麻将说得神乎其神,心里也有些好奇,于是索性由着这一老一少去胡闹,不再管他们。
学艺之前,萧环山首先告诫赵清源两条戒律:第一条是不可恃技自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越是身怀绝技,越是要低调,否则后患无穷;第二条是不可贪心过重,见好就收,贪念过重必定会引火烧身。
对于这两条戒律,赵清源自然是满口答应,萧环山这才开始教他打麻将的技艺。
所谓打麻将的技艺,说一千道一万,无非还是个作弊。但是,萧环山教给赵清源的作弊手段却远不是偷牌换张、钻桌子看牌等下三滥的招数。
一副麻将牌,除去花牌,总共一百三十六张。这一百三十六张牌的码放过程中,可以演变出若干种变化来,但只要用心观察和计算,便会从中发现一定的规律来,这就是所谓的“牌性”。打麻将的最高境界,就是计算“牌性”。
如果能掌握“牌性”,在码牌、掷色子之时,只要稍作技术练习,便可以做到想要什么牌,就来什么牌。
当然,要算清这一百三十六张麻将牌的“牌性”的确是桩苦差事,幸好赵清源在这方面天生就有灵性,一学就会,一教就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赵清源打麻将的技术也可以算得上是略有名堂了。
这一天,赵清源决定到附近的麻将馆里小试一下牛刀。跟赵清源同桌竞技的三位麻友都是“大牯牛”,对作弊的技巧一点都不懂。赵清源心想,好歹自己跟着师父学了半年多,要赢这三头“大牯牛”还不是小菜一碟?
可是,真下了场子,情况远没有赵清源想的那么简单。跟师父学艺时,师父在洗牌、码牌、掷色子等环节上动作做得很慢,并且一边做一边跟赵清源讲解,所以赵清源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手到牌来。但现在真到了牌桌上,这三头“大牯牛”洗牌时稀里哗啦一阵乱推、乱搓,赵清源别说算“牌性”了,连眼睛都不够用了,看都看不过来,哪儿还有心思去算计?
如此几圈打下来,萧环山传授的麻将技术,赵清源愣是一招都没用上,最后输得急了眼,赵清源只好又用起了过去常用的下三滥招数。结果,赵清源作弊不成,被牌友发现,三个牌友当场将赵清源按倒在地,要不是新近认识的一个叫陈四的麻友,在旁边全力劝阻,赵清源这次非头破血流不可。
经过这场大败之后,赵清源不由对萧环山的“麻仙”身份产生了怀疑,便去找萧环山,埋怨他教的麻将技术全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对此,萧环山微微一笑,也不解释,而是带着赵清源又去了附近那家麻将馆。
说来也凑巧,萧环山领着赵清源一进麻将馆,便又遇到了那三头“大牯牛”。那三人见赵清源又来打麻将,便对他冷嘲热讽。赵清源想要还嘴,却被萧环山摇手制止。
“三位朋友,我这个小徒弟不懂牌场上的规矩,前几天来这里丢人现眼了,”萧环山笑眯眯地说,“今天我带他来,一是向各位赔礼道歉,二是想跟各位再到麻将桌上切磋一下。”
赵清源不知道,这三个人原来并不是“大牯牛”,而是一伙儿的。打麻将之时,他们互相使眼色、打手势,合起伙来作弊,专骗赵清源这样的冤大头。此时,这三人一听萧环山主动送上门来,要跟他们较量牌技,不由心头暗喜,互相一使眼色,便乐呵呵地答应下来。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萧环山一下场子,情形便与赵清源截然不同了。只见萧环山气定神闲,掐指默算,谈笑之间有如神助,想要什么牌,伸手便能摸来。一时间是连连坐庄,使得三位同桌愁眉苦脸,一个劲儿骂娘。
在一旁观战的赵清源,心里那叫一个美。
一圈牌还没有打完,三位同桌口袋里的钱便被萧环山赢了个精光。身上没了钱,这三人只好连声骂着“邪门”,无可奈何地摇头认输。
直到此时,赵清源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了“麻仙”的手段,从此心悦诚服,安心跟着萧环山苦练麻将技艺。
话说赵清源跟着萧环山学艺整整一年之后,这天,萧环山突然告诉赵清源,他可以学成出山了,从今以后,不用再来找自己学习打麻将了。最后还特意告诫赵清源:“小赵,你只要牢记我曾经说过的那两条戒律,便不会惹出什么麻烦,还可保你吃喝不愁、一生平安。”
赵清源认真地点头答应,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萧环山的家。
自从学成出山之后,赵清源夫妻的生活渐渐宽裕起来。赵清源赢的钱越来越多,夫妻俩便卖掉了原先居住的小房子,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房子。这时,江晓蕾便劝赵清源收手:“打麻将终究不是个正经事,趁咱们手里还有些积蓄,不如拿出来开个饭店,只要咱好好干,还愁赚不来大钱?”
但是此时,赵清源正享受着打麻将所带来的快感,江晓蕾的话他哪里能听得进去?
3. 大庄
刚开始出来打麻将的时候,赵清源还谨记着萧环山的嘱咐,始终未触犯那两条戒律。但随着时日渐久,赵清源的打麻将技术日渐成熟,他不免滋长出一些骄傲的情绪来。渐渐的,萧环山嘱咐的那两条戒律便被赵清源抛在了脑后。此时的赵清源已经没有了在小麻将馆里打牌的兴致,一晚上大不了千八百块的输赢,实在提不起劲来。这一天,他听麻友陈四说,附近有一家地下黑赌场,那里面赌得很大,一把就是几万块钱的输赢。
赵清源听了,顿时来了兴趣,马上缠着陈四替他牵线,他要去大赌场里试试水。陈四答应了。
赌场的地点很神秘,只有在每天晚上才开放。参赌的人,首先要经过严格的身份检查,其次要在晚上八点钟之前,赶到百乐门大舞厅的后门会合,坐上一辆窗帘紧闭、没有牌照的大巴车,并且还要戴上特制的眼罩,然后司机才会开车带他们去赌场。
汽车弯弯曲曲一路颠簸,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这所地下大赌场。
赌场里的装修非常简陋,但是地方很大,大厅足有一千多平方米,还有大大小小的包间。
赵清源头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比较谨慎,打牌的时候故意有输有赢,一晚上下来,只不过才赢了一万多块钱,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来过几次之后,赵清源发现这里虽然赌得极大,但并没有什么高手,想来都是些有钱没处花的大款。赵清源想,遇到这种“菜鸟”,不狠狠地宰他们一把,简直就是犯罪。于是,赵清源渐渐地开始放开手脚,大把大把地赢钱。最厉害的一个晚上,竟然赢了十多万。
赵清源终于引起了大庄的注意。大庄也就是赌场里的老板,是个神秘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来历,就连赌场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他年纪不大,看上去顶多也不过四十岁。他长得很清秀,文质彬彬,经常穿着一件很随意的夹克衫,戴一副很普通的宽边近视眼镜,乍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中学教师一样。
在赌场里一个隐蔽的房间里,大庄面对着监视屏,问身边的人:“你们看清他的手法了吗?”
站在大庄身旁一位穿了一身黑西服的人犹豫不决地说:“看……看不大出来,好像是这小子运气特别好。”
大庄冷冷地说:“你相信一个人的赌运会一直这么好吗?”
黑西服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这个好像不太可能,不过……如果他是出老千,手上一定有动作,可是我们观察了他好几天,始终没发现他手上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笨蛋,”大庄冷冷地说,“你要是观察他的手,你一辈子也休想看出诀窍来。”
黑西服不解地问:“那……那诀窍在什么地方呢,老板?”
“在他脑子里,”大庄缓缓地说,“出老千的最高境界就是算‘牌性’,他现在用的就是这一招,一百三十六张麻将牌,全都印在了他脑子里。”
“妈的,这小子是什么来路?竟然敢到咱们场子里来捣乱,”黑西服说,“老板,我找几个兄弟,把他给做了,怎么样?”
“扯淡,敢开赌场就不能怕人家出老千,牌桌上的事情只能通过牌桌来解决,”大庄若有所思地说,“况且,这个人所使的这种招数,一般人根本不会用,除非……除非他跟传说中的那个东北麻仙有什么关连。”
4. 设局
这天,赵清源正摸着牌,忽然一个穿黑西服的人走过来跟他搭讪:“朋友,我看你手气挺顺,想不想玩点儿更大的?”
赵清源不动声色地反问:“你们这里还有更大的?”
黑西服说:“当然,我们这里专门设有贵宾室,那里边玩儿可比这些大多了。”
“是吗?”赵清源有点动心了,说,“玩不玩再说,先过去看看也行。”
黑西服彬彬有礼地说:“非常欢迎。”
贵宾室里的装修明显要比外边豪华气派得多,墙上挂着洁白的阿富汗壁毯,屋顶悬挂着菲律宾水晶吊灯,欧式的落地窗紧闭着,遮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天鹅绒窗帘。
贵宾室的麻将桌前,坐着两个肥头大耳、一脸蠢相的胖子,加上这个带他来的黑西服,一共是四个人,正好凑够一桌。
赵清源并没有急着坐下来,而是略怀戒心地问:“玩多大的?”
黑西服说:“五毛钱一张,行吗?”赵清源知道,在赌场上,通常所说的一毛就是一万。
赵清源满不在乎地说:“好哇,这才够刺激。”
“是啊,是啊,输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够刺激才行。”肥胖子傻笑说。
漂亮的服务小姐端着金灿灿的托盘,将各色筹码均匀地分送到了四个人的面前。接下来,牌局开始了。
一开始,赵清源打得还算顺利,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其他三个人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而赵清源面前的筹码堆成了小山。赵清源在心里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至少赢了一百多万。
打到第四圈的时候,黑西服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已经三点了,咱们再打最后一圈,这样吧,反正手里还有这么多筹码没输完,索性全都输给赵兄得了,咱们再加大一倍筹码,怎么样?”
两个胖子也全都答应,说:“反正输赢也无所谓,越刺激越好。”
赵清源犹豫了一下,也答应了。赵清源之所以敢答应,那是因为几圈打下来,他已经发现,同桌的这三个麻友虽然出手大方,但打起麻将来全是“菜鸟”。跟这种人打牌,赌注再大也不用怕。
可是,第四圈一开打,赵清源便发现自己上当了。
这三个人的牌路一下全变了,坐在他上家的黑西服突然开始憋他,赵清源出什么牌,黑西服便喂他什么牌,而坐在赵清源下家的胖子又拼命地用好张去喂另一个胖子。于是,牌局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坐在赵清源对面的胖子开始把把和牌。
直到此时,赵清源才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这三个人是一伙儿的,这是联合起来要整他。
赵清源把面前的麻将牌一推,说:“朋友,你们要是这样,咱们可就没法玩儿了。”
“你什么意思?我们怎样了?”黑西服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难看,说,“打牌随心意,我们想怎么出牌就怎么出,你管得着吗?”
赵清源愤愤地说:“好,我管不着,我不玩儿了总行吧?”
“不行,必须打完这一圈才能起身,这是牌桌上的规矩。”坐在赵清源对面的胖子阴森森地说。
赵清源无奈,只好又坐了下来。
这一坐不要紧,赵清源对面的胖子竟然连坐二十多把庄,赵清源面前的筹码输了个干干净净。
赵清源铁青着脸说:“按照牌桌上的规矩,筹码输光了,这下总可以不玩了吧!”
“好,可以,”黑西服微笑着指挥一个胖子,说,“把兑换筹码的小姐喊来,让这位赵兄掏钱。”
赵清源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一晚上,大约输了一百多万元。赵清源不由有些懊恼,暗骂自己糊涂,中了人家的暗算。
这时,服务小姐进来了,只听她轻声细语地对赵清源说:“先生,您输掉的筹码一共是一千两百万元。”
赵清源仿佛是听到了一声惊雷似的,吓得一下就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什么,多少?”赵清源一脸惊骇地说,“不是五毛钱一张吗?”
“是五毛呀,”服务小姐笑眯眯地说,“贵宾室里的五毛跟外面大厅里的五毛不一样,外面一毛是一万,贵宾室里一毛是十万。”
赵清源急了,开口就骂:“妈的,你们摆明了要玩儿我!”
黑西服阴沉着脸说:“嘴巴放干净点,谁玩儿你了,这是这里的规矩,不信你找外面那些老顾客打听打听,他们全都知道。”
5. 圈套
天刚蒙蒙亮,江晓蕾便接到了赵清源的求救电话:“喂,媳妇快救救我。”
江晓蕾一头雾水地问:“怎么了清源,出什么事了?”
“我赌钱输了,现在被人扣押起来了,他们让我打电话给你,” 赵清源在一间黑漆漆的小屋子里,拿着手机,垂头丧气地说,“你去请萧大爷来,只有他能救我。”
江晓蕾焦急地问:“你输了多少钱,咱们给他们不就得了?”
赵清源结巴着说:“给不起,我……我输了一千多万。”
“天呐,”江晓蕾发出一声惊叫,“你疯啦!”
“不是的媳妇,他们……他们合起伙来骗我。”赵清源压低了声音说。
在一旁监视赵清源的黑西服突然恶声说:“少废话,谁骗你,再这么说小心老子打掉你的狗牙。”
“是是是,不敢了,”赵清源忙说,“媳妇,你别问了,快去请萧大爷吧,可千万别报警,他们说你要是敢报警,就会杀了我。他们只是想跟萧大爷赌一把,无论输赢,都会放我走的。你请来萧大爷后,去找陈四,他知道什么时间,到哪里坐车。”
放下赵清源的电话,江晓蕾不敢怠慢,直奔萧环山的住处。
“萧大爷,这一次你一定要救赵清源的命,否则……否则便没人能救他了。”一见到萧环山,江晓蕾便流出泪来。
萧环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
接着,江晓蕾便把赵清源打电话说的事情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萧环山听完,拧紧了眉头,半天不语。
江晓蕾哀求道:“萧大爷,你可一定要救救清源呀!”
“我早告诫过他不可恃技自傲,不可贪心不足,可是显然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所以才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萧环山拧着眉头说,“现在人家是来者不善,即便我出面,也未必能救得了他。”
“您可千万不能不管呀,当初,我就不同意他跟您学打麻将,可是你们两个,一个执意要教,一个执意要学,现在学出了麻烦,您可不能不管。”
萧环山摇着头,叹着气说:“放心吧,你们两口子救过我的命,这个事我一定会管。”
陈四很快便联系上了。但陈四有个要求,让萧环山带他一块儿去赌场,他要亲眼见识一下这场难得一见的赌神大战。
入夜的时候,陈四已经替萧环山跟赌场接上了头,按照赌场的指示,陈四带着萧环山来到百乐门大舞厅后门,有一辆黑色奔驰轿车早就在那里恭候他们了。萧环山与陈四上了车,戴上眼罩,便直奔地下赌场而去。
牌局依然设在贵宾室里,不过牌桌上的人却换了一半。那两个胖子还在,不过黑西服的位置上却换成了穿夹克衫的中年人。黑西服垂着手,小心翼翼地站在夹克衫的身后。
赵清源精神委靡、满脸惊恐地缩在墙角,看到萧环山进来,仿佛见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样,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坐吧。”夹克衫文质彬彬地一伸手,示意萧环山坐下。
萧环山人还没有入坐,先问规矩:“怎么赌?”
夹克衫胸有成竹地说:“这里你年纪最大,规矩由你定,怎么样?”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咱们就玩推倒和,不论大小牌,一把定输赢,好吗?”萧环山知道宴无好宴,局无好局,如果能够速战速决那是最好,否则时间一长,难免会有闪失。
“爽快,麻仙果然不愧是麻仙,一把定输赢,有气魄,就这么定了,”夹克衫不动声色地说,“不过,规矩你定,赌注要由我来定,你要是赢了,你就可以带着赵清源平安离开这里;但你要是输了,赵清源可以走,你却得留下一双手。”
萧环山沉吟了一下,沉声说:“好,我赌了。”
萧环山坐下,开始缓慢地洗牌。萧环山虽然老了,但是他的那双手却依然干净、稳定。
牌已经码好,色子也已掷出。这一把,由萧环山做庄。萧环山抓牌的手,伸出去很缓慢,但非常坚定有力,仿佛他要去抓的不是麻将牌,而是敌人的咽喉。
十四张麻将牌抓完了,萧环山却迟迟不肯出牌。坐在萧环山下家的胖子忍不住了,便催促说:“你还打不打?赶快出牌呀。”
萧环山笑了,说:“我好像是抓了一把天和牌,不用再出了。”说着,萧环山缓缓地将手中的麻将牌一齐推倒。只见萧环山手里这把牌分别是四五六筒、五六七条、七八九万、三个红中、一对二万。
贵宾室里发出一片啧啧惊叹声,除了大庄,其他人不由全都看直了眼,就连赵清源也在心中惊叹:“麻仙不愧是麻仙,就凭这一手,恐怕自己一辈子都学不会。”
萧环山缓缓地说:“不好意思,虽然是把小屁和,但终归还是和牌了,人,我可就要带走了。”
“慢着。”大庄一摆手说。
“怎么?莫非你想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值千金,说出口的话,我当然不会反悔,”大庄微笑着说,“可是,你看仔细了,这把牌,你可是诈和。”
“不可能……”萧环山这句话还未说完,便张大了嘴巴,再也说不下去了。那是因为,他忽然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推倒的这副牌里,明明有一张四筒、一张五筒、一张六筒,可是现在那张五筒竟然不翼而飞了,而是变成了一对四筒加一张六筒。
“按照牌桌上的规矩,诈和要赔三家,”大庄得意地笑着说,“所以,这把牌输的不是我们,而是你!”
6. 真相
萧环山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片死灰。“愿赌服输,我输了,这双手你可以随时拿走,”萧环山一脸戚色地说,“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我的那张五筒为什么会变成四筒,不知可否相告?”
大庄得意地大笑道:“说穿了很简单,那是因为在这副麻将牌上,我想把哪张牌变掉就随时可以变掉。”大庄说着,手腕一翻,掌心里露出一个烟盒般大小的遥控器来。
只见大庄轻轻一按遥控器,萧环山面前的那两张四筒的中心部位突然便多出一个圆圈来,于是四筒变成了五筒,大庄再一按遥控器,萧环山面前那一对二万牌上方突然多出了一杠,于是二万变成了三万。
赵清源扑过来说:“你……你耍赖,这把不算。”
“退下,”萧环山阴沉着脸说,“既是赌博,又有几个不耍赖的,我们不也是一样吗?人家技高一筹,萧某人今天输得心服口服。”萧环山说着,将双手缓缓地放到桌子上,说,“手在这里,拿去吧!”
大庄的脸色变了,不再是得意的神情,而是变得有些怪异,既像是有些兴奋,又像是有些痛苦,还有一些迷茫和无助。
“刀!”大庄从牙缝里冷冷地挤出了一个字。
站在大庄身后的黑西服马上从怀里掏出一把又窄又锋利的西瓜刀来,交给大庄。
赵清源闭上眼,流出泪来,祸是他惹出来的,现在他实在无颜去看这残忍的一幕。
“等待这一天,我已等了三十八年,”大庄眼睛里闪出深邃的痛苦之色,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地说,“你终于也有了今天。”
“你是谁?”萧环山诧异地问,“三十八年?你我之间难道曾经有什么过节?”
“你当然不会认识我,”大庄发出了一串近乎疯狂的笑声,“因为我一出生,你便抛弃了我和我母亲。这些年来,为了找到你,我遍访天下赌场,练就了一身的赌艺,也闯出了一个赌王的名号,我练赌术、开赌场,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你,替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你……你是麟儿?”萧环山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你总算想起我来了。”
萧环山一下站起来,眼里涌出了两行老泪:“你真的是我的麟儿?”
大庄狠狠地说:“我不是你的麟儿,从三十八年前你抛弃了我们母子那天起,我便不再是你的儿子。”
“你错了,孩子,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抛弃你们母子俩,”萧环山流着泪,摇着头说,“是你母亲……她不想再见我了,因为……因为我伤透了她的心。”
大庄愣了。
“她一直反对我打麻将,可是……可是我始终无法戒掉麻将瘾,”萧环山喃喃地说,“就在你出生的那天晚上,我还是没肯在家陪陪你妈,而是跟着几个牌友,烂赌了一夜,从那一天起,你母亲便对我彻底绝望了,在你刚刚满月的时候,她便抱着你不辞而别。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明白,在我的生命里,最珍贵的根本不是什么麻将,也不是什么麻仙的名头,而是你们母子。此后的三十八年里,我走遍天涯海角,想找寻你们母子,可始终也没能找到。你知道吗?孩子,这三十八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除了你的母亲,我这一生再也没有碰过任何女人,那是因为我始终都深爱着你们。”
大庄喃喃地说:“我……我不信。”
“信也好,不信也好,”萧环山含着泪、笑着说,“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不过在我死之前,还能亲眼看到你,即便死我也瞑目了。”
大庄握刀的手开始发抖。
“我能证明,这些年,萧大爷真的是独自生活,”赵清源急忙证明说,“他老人家身边真的没有别的女人,现在既然都解释清楚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还要动刀动枪的呢?”
大庄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起来,握刀的手抖动得更加厉害了。然而就在这时,突然有一把枪顶住了大庄的脑袋。
握枪的不是别人,居然是毫不起眼的小角色陈四。
“放下你的刀,赌王萧麟,”陈四冷冷地说,“你的赌场现在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赵清源急忙说:“陈四,你开什么玩笑?大家都是自己人,快放下枪。”
“谁有空跟你们开玩笑,我是一名卧底警察,为了找出狡猾的赌王萧麟,我们可真是费了不少工夫,”陈四盯着大庄的眼睛说,“他隐藏得很深,我们几次抓捕,都被他狡猾地溜掉了,所以我才会把赵清源推荐到这里来。因为我知道,赵清源的赌技很高,并且在赵清源背后还有一位麻仙在撑腰,要对付这两个人,必须得赌王亲自出马。”
陈四正说着,外面突然闯进一个赌场的马仔:“老板,不好了,外面全是警察……”马仔说到这里时,才看到了顶在大庄脑袋上的那把手枪,于是,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辆辆闪动着警灯的警车密密麻麻地停在了赌场周围,一个个赌徒被警察押解着,垂头丧气地从赌场里走了出来。
“孩子,是我害了你,我罪该万死。”萧环山被一名警察押着走向一辆警车的时候,突然扭回头,冲萧麟狂喊了一句。然后,他便像疯了一样,挣脱警察的手臂,一头向警车撞去。
萧环山倒在了地上,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
“爸爸……”萧麟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声。
汽车弯弯曲曲一路颠簸,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这所地下大赌场。
赌场里的装修非常简陋,但是地方很大,大厅足有一千多平方米,还有大大小小的包间。
赵清源头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比较谨慎,打牌的时候故意有输有赢,一晚上下来,只不过才赢了一万多块钱,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来过几次之后,赵清源发现这里虽然赌得极大,但并没有什么高手,想来都是些有钱没处花的大款。赵清源想,遇到这种“菜鸟”,不狠狠地宰他们一把,简直就是犯罪。于是,赵清源渐渐地开始放开手脚,大把大把地赢钱。最厉害的一个晚上,竟然赢了十多万。
赵清源终于引起了大庄的注意。大庄也就是赌场里的老板,是个神秘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来历,就连赌场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他年纪不大,看上去顶多也不过四十岁。他长得很清秀,文质彬彬,经常穿着一件很随意的夹克衫,戴一副很普通的宽边近视眼镜,乍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中学教师一样。
在赌场里一个隐蔽的房间里,大庄面对着监视屏,问身边的人:“你们看清他的手法了吗?”
站在大庄身旁一位穿了一身黑西服的人犹豫不决地说:“看……看不大出来,好像是这小子运气特别好。”
大庄冷冷地说:“你相信一个人的赌运会一直这么好吗?”
黑西服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这个好像不太可能,不过……如果他是出老千,手上一定有动作,可是我们观察了他好几天,始终没发现他手上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笨蛋,”大庄冷冷地说,“你要是观察他的手,你一辈子也休想看出诀窍来。”
黑西服不解地问:“那……那诀窍在什么地方呢,老板?”
“在他脑子里,”大庄缓缓地说,“出老千的最高境界就是算‘牌性’,他现在用的就是这一招,一百三十六张麻将牌,全都印在了他脑子里。”
“妈的,这小子是什么来路?竟然敢到咱们场子里来捣乱,”黑西服说,“老板,我找几个兄弟,把他给做了,怎么样?”
“扯淡,敢开赌场就不能怕人家出老千,牌桌上的事情只能通过牌桌来解决,”大庄若有所思地说,“况且,这个人所使的这种招数,一般人根本不会用,除非……除非他跟传说中的那个东北麻仙有什么关连。”
4. 设局
这天,赵清源正摸着牌,忽然一个穿黑西服的人走过来跟他搭讪:“朋友,我看你手气挺顺,想不想玩点儿更大的?”
赵清源不动声色地反问:“你们这里还有更大的?”
黑西服说:“当然,我们这里专门设有贵宾室,那里边玩儿可比这些大多了。”
“是吗?”赵清源有点动心了,说,“玩不玩再说,先过去看看也行。”
黑西服彬彬有礼地说:“非常欢迎。”
贵宾室里的装修明显要比外边豪华气派得多,墙上挂着洁白的阿富汗壁毯,屋顶悬挂着菲律宾水晶吊灯,欧式的落地窗紧闭着,遮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天鹅绒窗帘。
贵宾室的麻将桌前,坐着两个肥头大耳、一脸蠢相的胖子,加上这个带他来的黑西服,一共是四个人,正好凑够一桌。
赵清源并没有急着坐下来,而是略怀戒心地问:“玩多大的?”
黑西服说:“五毛钱一张,行吗?”赵清源知道,在赌场上,通常所说的一毛就是一万。
赵清源满不在乎地说:“好哇,这才够刺激。”
“是啊,是啊,输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够刺激才行。”肥胖子傻笑说。
漂亮的服务小姐端着金灿灿的托盘,将各色筹码均匀地分送到了四个人的面前。接下来,牌局开始了。
一开始,赵清源打得还算顺利,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其他三个人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而赵清源面前的筹码堆成了小山。赵清源在心里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至少赢了一百多万。
打到第四圈的时候,黑西服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已经三点了,咱们再打最后一圈,这样吧,反正手里还有这么多筹码没输完,索性全都输给赵兄得了,咱们再加大一倍筹码,怎么样?”
两个胖子也全都答应,说:“反正输赢也无所谓,越刺激越好。”
赵清源犹豫了一下,也答应了。赵清源之所以敢答应,那是因为几圈打下来,他已经发现,同桌的这三个麻友虽然出手大方,但打起麻将来全是“菜鸟”。跟这种人打牌,赌注再大也不用怕。
可是,第四圈一开打,赵清源便发现自己上当了。
这三个人的牌路一下全变了,坐在他上家的黑西服突然开始憋他,赵清源出什么牌,黑西服便喂他什么牌,而坐在赵清源下家的胖子又拼命地用好张去喂另一个胖子。于是,牌局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坐在赵清源对面的胖子开始把把和牌。
直到此时,赵清源才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这三个人是一伙儿的,这是联合起来要整他。
赵清源把面前的麻将牌一推,说:“朋友,你们要是这样,咱们可就没法玩儿了。”
“你什么意思?我们怎样了?”黑西服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难看,说,“打牌随心意,我们想怎么出牌就怎么出,你管得着吗?”
赵清源愤愤地说:“好,我管不着,我不玩儿了总行吧?”
“不行,必须打完这一圈才能起身,这是牌桌上的规矩。”坐在赵清源对面的胖子阴森森地说。
赵清源无奈,只好又坐了下来。
这一坐不要紧,赵清源对面的胖子竟然连坐二十多把庄,赵清源面前的筹码输了个干干净净。
赵清源铁青着脸说:“按照牌桌上的规矩,筹码输光了,这下总可以不玩了吧!”
“好,可以,”黑西服微笑着指挥一个胖子,说,“把兑换筹码的小姐喊来,让这位赵兄掏钱。”
赵清源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一晚上,大约输了一百多万元。赵清源不由有些懊恼,暗骂自己糊涂,中了人家的暗算。
这时,服务小姐进来了,只听她轻声细语地对赵清源说:“先生,您输掉的筹码一共是一千两百万元。”
赵清源仿佛是听到了一声惊雷似的,吓得一下就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什么,多少?”赵清源一脸惊骇地说,“不是五毛钱一张吗?”
“是五毛呀,”服务小姐笑眯眯地说,“贵宾室里的五毛跟外面大厅里的五毛不一样,外面一毛是一万,贵宾室里一毛是十万。”
赵清源急了,开口就骂:“妈的,你们摆明了要玩儿我!”
黑西服阴沉着脸说:“嘴巴放干净点,谁玩儿你了,这是这里的规矩,不信你找外面那些老顾客打听打听,他们全都知道。”
5. 圈套
天刚蒙蒙亮,江晓蕾便接到了赵清源的求救电话:“喂,媳妇快救救我。”
江晓蕾一头雾水地问:“怎么了清源,出什么事了?”
“我赌钱输了,现在被人扣押起来了,他们让我打电话给你,” 赵清源在一间黑漆漆的小屋子里,拿着手机,垂头丧气地说,“你去请萧大爷来,只有他能救我。”
江晓蕾焦急地问:“你输了多少钱,咱们给他们不就得了?”
赵清源结巴着说:“给不起,我……我输了一千多万。”
“天呐,”江晓蕾发出一声惊叫,“你疯啦!”
“不是的媳妇,他们……他们合起伙来骗我。”赵清源压低了声音说。
在一旁监视赵清源的黑西服突然恶声说:“少废话,谁骗你,再这么说小心老子打掉你的狗牙。”
“是是是,不敢了,”赵清源忙说,“媳妇,你别问了,快去请萧大爷吧,可千万别报警,他们说你要是敢报警,就会杀了我。他们只是想跟萧大爷赌一把,无论输赢,都会放我走的。你请来萧大爷后,去找陈四,他知道什么时间,到哪里坐车。”
放下赵清源的电话,江晓蕾不敢怠慢,直奔萧环山的住处。
“萧大爷,这一次你一定要救赵清源的命,否则……否则便没人能救他了。”一见到萧环山,江晓蕾便流出泪来。
萧环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
接着,江晓蕾便把赵清源打电话说的事情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萧环山听完,拧紧了眉头,半天不语。
江晓蕾哀求道:“萧大爷,你可一定要救救清源呀!”
“我早告诫过他不可恃技自傲,不可贪心不足,可是显然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所以才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萧环山拧着眉头说,“现在人家是来者不善,即便我出面,也未必能救得了他。”
“您可千万不能不管呀,当初,我就不同意他跟您学打麻将,可是你们两个,一个执意要教,一个执意要学,现在学出了麻烦,您可不能不管。”
萧环山摇着头,叹着气说:“放心吧,你们两口子救过我的命,这个事我一定会管。”
陈四很快便联系上了。但陈四有个要求,让萧环山带他一块儿去赌场,他要亲眼见识一下这场难得一见的赌神大战。
入夜的时候,陈四已经替萧环山跟赌场接上了头,按照赌场的指示,陈四带着萧环山来到百乐门大舞厅后门,有一辆黑色奔驰轿车早就在那里恭候他们了。萧环山与陈四上了车,戴上眼罩,便直奔地下赌场而去。
牌局依然设在贵宾室里,不过牌桌上的人却换了一半。那两个胖子还在,不过黑西服的位置上却换成了穿夹克衫的中年人。黑西服垂着手,小心翼翼地站在夹克衫的身后。
赵清源精神委靡、满脸惊恐地缩在墙角,看到萧环山进来,仿佛见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样,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坐吧。”夹克衫文质彬彬地一伸手,示意萧环山坐下。
萧环山人还没有入坐,先问规矩:“怎么赌?”
夹克衫胸有成竹地说:“这里你年纪最大,规矩由你定,怎么样?”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咱们就玩推倒和,不论大小牌,一把定输赢,好吗?”萧环山知道宴无好宴,局无好局,如果能够速战速决那是最好,否则时间一长,难免会有闪失。
“爽快,麻仙果然不愧是麻仙,一把定输赢,有气魄,就这么定了,”夹克衫不动声色地说,“不过,规矩你定,赌注要由我来定,你要是赢了,你就可以带着赵清源平安离开这里;但你要是输了,赵清源可以走,你却得留下一双手。”
萧环山沉吟了一下,沉声说:“好,我赌了。”
萧环山坐下,开始缓慢地洗牌。萧环山虽然老了,但是他的那双手却依然干净、稳定。
牌已经码好,色子也已掷出。这一把,由萧环山做庄。萧环山抓牌的手,伸出去很缓慢,但非常坚定有力,仿佛他要去抓的不是麻将牌,而是敌人的咽喉。
十四张麻将牌抓完了,萧环山却迟迟不肯出牌。坐在萧环山下家的胖子忍不住了,便催促说:“你还打不打?赶快出牌呀。”
萧环山笑了,说:“我好像是抓了一把天和牌,不用再出了。”说着,萧环山缓缓地将手中的麻将牌一齐推倒。只见萧环山手里这把牌分别是四五六筒、五六七条、七八九万、三个红中、一对二万。
贵宾室里发出一片啧啧惊叹声,除了大庄,其他人不由全都看直了眼,就连赵清源也在心中惊叹:“麻仙不愧是麻仙,就凭这一手,恐怕自己一辈子都学不会。”
萧环山缓缓地说:“不好意思,虽然是把小屁和,但终归还是和牌了,人,我可就要带走了。”
“慢着。”大庄一摆手说。
“怎么?莫非你想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值千金,说出口的话,我当然不会反悔,”大庄微笑着说,“可是,你看仔细了,这把牌,你可是诈和。”
“不可能……”萧环山这句话还未说完,便张大了嘴巴,再也说不下去了。那是因为,他忽然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推倒的这副牌里,明明有一张四筒、一张五筒、一张六筒,可是现在那张五筒竟然不翼而飞了,而是变成了一对四筒加一张六筒。
“按照牌桌上的规矩,诈和要赔三家,”大庄得意地笑着说,“所以,这把牌输的不是我们,而是你!”
6. 真相
萧环山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片死灰。“愿赌服输,我输了,这双手你可以随时拿走,”萧环山一脸戚色地说,“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我的那张五筒为什么会变成四筒,不知可否相告?”
大庄得意地大笑道:“说穿了很简单,那是因为在这副麻将牌上,我想把哪张牌变掉就随时可以变掉。”大庄说着,手腕一翻,掌心里露出一个烟盒般大小的遥控器来。
只见大庄轻轻一按遥控器,萧环山面前的那两张四筒的中心部位突然便多出一个圆圈来,于是四筒变成了五筒,大庄再一按遥控器,萧环山面前那一对二万牌上方突然多出了一杠,于是二万变成了三万。
赵清源扑过来说:“你……你耍赖,这把不算。”
“退下,”萧环山阴沉着脸说,“既是赌博,又有几个不耍赖的,我们不也是一样吗?人家技高一筹,萧某人今天输得心服口服。”萧环山说着,将双手缓缓地放到桌子上,说,“手在这里,拿去吧!”
大庄的脸色变了,不再是得意的神情,而是变得有些怪异,既像是有些兴奋,又像是有些痛苦,还有一些迷茫和无助。
“刀!”大庄从牙缝里冷冷地挤出了一个字。
站在大庄身后的黑西服马上从怀里掏出一把又窄又锋利的西瓜刀来,交给大庄。
赵清源闭上眼,流出泪来,祸是他惹出来的,现在他实在无颜去看这残忍的一幕。
“等待这一天,我已等了三十八年,”大庄眼睛里闪出深邃的痛苦之色,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地说,“你终于也有了今天。”
“你是谁?”萧环山诧异地问,“三十八年?你我之间难道曾经有什么过节?”
“你当然不会认识我,”大庄发出了一串近乎疯狂的笑声,“因为我一出生,你便抛弃了我和我母亲。这些年来,为了找到你,我遍访天下赌场,练就了一身的赌艺,也闯出了一个赌王的名号,我练赌术、开赌场,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你,替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你……你是麟儿?”萧环山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你总算想起我来了。”
萧环山一下站起来,眼里涌出了两行老泪:“你真的是我的麟儿?”
大庄狠狠地说:“我不是你的麟儿,从三十八年前你抛弃了我们母子那天起,我便不再是你的儿子。”
“你错了,孩子,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抛弃你们母子俩,”萧环山流着泪,摇着头说,“是你母亲……她不想再见我了,因为……因为我伤透了她的心。”
大庄愣了。
“她一直反对我打麻将,可是……可是我始终无法戒掉麻将瘾,”萧环山喃喃地说,“就在你出生的那天晚上,我还是没肯在家陪陪你妈,而是跟着几个牌友,烂赌了一夜,从那一天起,你母亲便对我彻底绝望了,在你刚刚满月的时候,她便抱着你不辞而别。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明白,在我的生命里,最珍贵的根本不是什么麻将,也不是什么麻仙的名头,而是你们母子。此后的三十八年里,我走遍天涯海角,想找寻你们母子,可始终也没能找到。你知道吗?孩子,这三十八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除了你的母亲,我这一生再也没有碰过任何女人,那是因为我始终都深爱着你们。”
大庄喃喃地说:“我……我不信。”
“信也好,不信也好,”萧环山含着泪、笑着说,“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不过在我死之前,还能亲眼看到你,即便死我也瞑目了。”
大庄握刀的手开始发抖。
“我能证明,这些年,萧大爷真的是独自生活,”赵清源急忙证明说,“他老人家身边真的没有别的女人,现在既然都解释清楚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还要动刀动枪的呢?”
大庄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起来,握刀的手抖动得更加厉害了。然而就在这时,突然有一把枪顶住了大庄的脑袋。
握枪的不是别人,居然是毫不起眼的小角色陈四。
“放下你的刀,赌王萧麟,”陈四冷冷地说,“你的赌场现在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赵清源急忙说:“陈四,你开什么玩笑?大家都是自己人,快放下枪。”
“谁有空跟你们开玩笑,我是一名卧底警察,为了找出狡猾的赌王萧麟,我们可真是费了不少工夫,”陈四盯着大庄的眼睛说,“他隐藏得很深,我们几次抓捕,都被他狡猾地溜掉了,所以我才会把赵清源推荐到这里来。因为我知道,赵清源的赌技很高,并且在赵清源背后还有一位麻仙在撑腰,要对付这两个人,必须得赌王亲自出马。”
陈四正说着,外面突然闯进一个赌场的马仔:“老板,不好了,外面全是警察……”马仔说到这里时,才看到了顶在大庄脑袋上的那把手枪,于是,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辆辆闪动着警灯的警车密密麻麻地停在了赌场周围,一个个赌徒被警察押解着,垂头丧气地从赌场里走了出来。
“孩子,是我害了你,我罪该万死。”萧环山被一名警察押着走向一辆警车的时候,突然扭回头,冲萧麟狂喊了一句。然后,他便像疯了一样,挣脱警察的手臂,一头向警车撞去。
萧环山倒在了地上,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
“爸爸……”萧麟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发出一声嘶哑的吼叫声。
零七网部分新闻及文章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若有涉及作者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删除或按规定办理。感谢所有提供资讯的网站,欢迎各类媒体与零七网进行文章共享合作。
零七广告

零七广告

零七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