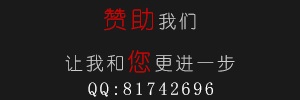高考结束的夏天,在等待分数和命运给予答案的不安中,炳恩想给出些什么承诺给雅宁。于是他和那时很多不知好歹的男孩子一样,在小纹身店里把雅宁的名字纹在了自己的肋骨上。雅宁看见他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可拦也拦不住。
大学四年,共同经历青春期的两个人没能熬过磨人的异地恋。第一个学期,两个人甘愿把父母给的生活费省吃俭用地献给了铁道事业。有时候见面,没有钱吃大餐,雅宁和炳恩就一人一口分吃一个烧饼夹肉,谁都不舍得把肉多咬一口,留给对方吃。
再后来,就是在猜疑之后漫漫无期地争吵,直到电话欠费停机才算休战。后来都想清楚了,为什么要和一个离你千里之外的人痴缠折磨呢?于是在两个人各自背着对方出轨之后,和平地分了手。
每个人的青春期里总有过这样一段生动鲜活的故事,像是一颗话梅一样让人念起就口舌生津。细细品评之后,怎么也琢磨不出当初为什么会做了那样的选择。
大学毕业的当天,雅宁拖了两个大箱子和同学们挥手道别,从一个北方小城买了火车硬座车票抵达了北京。从北京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外走,满满的都是汗臭味,还有沙尘暴的味道。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藕断丝连必定是一次狭路相逢,那么雅宁和炳恩的重逢绝对是一个最佳的注解。雅宁茫然地跟着中介去找寻合租的卧室单间,正当中介操着一口标准的广东普通话介绍这间次卧的采光如何比主卧优越,冬天暖气多么舒适的时候,炳恩穿着一件白T恤睡眼惺忪的从主卧门里走出来,还和中介打了声招呼:“哎,带人来看房啊。”
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愣住了。
起先他们是彼此和睦的合租室友,后来,雅宁就地把行李拖进了主卧。
一次炳恩晚上洗完澡光着膀子从浴室出来,雅宁终于没忍住,看着他左侧肋骨那个糊成一团的自己的名字的纹身印子说:“后来,怎么跟别的姑娘解释它的?”
炳恩说:“有什么好解释的,谁没年少无知过。”
“有后悔过么。”顿了一下,雅宁悄悄问。
炳恩问:“你指的什么。”
“没什么。”她转身又去做别的事。
有句话被讲得烂俗:如果你特别想得到一样东西,放开它,如果还会回来,那么注定就是属于你的。
人们几乎把这个道理信奉为真理,于是众人都以为,雅宁和炳恩如此的久别重逢,一定是上帝安排的命中注定。没别的选择,俩人就非得在一起过日子了。
那时雅宁在公关公司做实习生,几乎每个周末都在闹市区跑活动,常常是穿着连衣裙高跟鞋,扛起十多斤重的物料就狂奔到下一个活动地点。一宿一宿地盯搭建,第二天敷个面膜化了浓妆又是一副动力满满的样子。
炳恩常对她说:“你知道吗,你们老板看见有你这么拼命的实习生,一定特别感动,你这可真是拼自己的命给他赚钱。”
雅宁说:“新人么,不就是用来挡枪子儿的。一茬又一茬,谁会心疼。”
“我心疼啊。”炳恩说。
雅宁有时候觉得很难界定“心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她是否应该为炳恩的这种体验觉得愧疚。作为一个合格的女朋友,不是应该让恋人整日觉得心暖暖的才对吗,可炳恩的心是疼的。她总觉得自己是不怎么称职的。
她开始学着在周末不加班的时候做些好吃的来弥补心里的这种愧疚,她看着炳恩把可乐鸡翅的汤汁一滴不剩地拌进米饭的时候就想,他是会原谅她为了生存在这个城市里让他不安的过失了吧。
雅宁意料之中的迅速升职,成了他们公司里最年轻的经理。她熬黑了的眼眶在公司的会议室里被众人或是嫉妒或是羡慕地围观着,老板笑呵呵地说:“要继续努力,前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你。”
她是快乐的,又不免有些心酸。那是一种爬上了一座期待征服已久的山峰,可抵达后看到的又不是想象中的风景的失落。她想把这种讲不清的复杂心事分享给炳恩听,让她知道她光鲜外表之下那份阴暗的不安。
可当她拿着前台新印好的名片给他看的时候,他眼睛都没抬的咕哝了一句:“噢,升职啦,恭喜喔。”一个人趿拉着拖鞋出门去了。雅宁一肚子不成形的话正等着他来分析解答,哪知又被搁置成一锅浓稠的粥。
在北京过的日子,路途大多像是一次从大海向沙滩的迁徙,起初的脚步迟缓沉重,在泥泞里摔打,然后渐渐走向平缓舒适。雅宁和炳恩的生活也是如此。从吃饭算计着哪一个馆子的家常菜分大量足,到后来俩人点一桌子招牌菜吃罢剩了多半也不心疼。
他们从起初共用一个简陋的收纳箱,到两人分别拥有各自的大衣柜,里面用来摆放那些只能干洗的高档西装和衬衫。
青梅竹马的两个人,讨论起婚事已顺理成章。准备的婚房是租下的房东未住过的新房,雅宁手里整天捏着一个家居清单,筹备着采买婚后使用的全新日用品。她把守了多年的基金卖了,终于把那件自己最喜欢的婚纱买回家。衣柜里放不下,就用防尘袋盖着,挂在门后面,出来进去都忍不住摸两下。
炳恩有时候开玩笑说:“买婚纱多不实用啊,穿一天就搁置了,不如租。”
雅宁不屑地说:“新郎官也就当一天,我能不能去租一个?”
启程回老家领结婚证的那天是周一,周末的时候雅宁刚刚给客户做完一个新品发布会,庆功宴上喝得烂醉如泥。早晨醒来满身都是酒臭气,她晃晃荡荡地要起床洗澡,炳恩说:“你昨天醉成那样子,不如好好休息改天再去领证。”
雅宁半睁着眼说:“不行,这日子提前俩月就定了,我今天把工作都排开了,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返回家乡的飞机上,雅宁觉得头很痛,她歪过头看到炳恩不是太高兴的样子,想大概是因为自己身体不舒服影响他的好心情了吧。
炳恩是在雅宁第三十七次在家里试穿婚纱时候提出分手的,那天他们的结婚证刚刚到手一个月,离婚礼还差十二天。
一连串的“对不起”像是从天而降的冰雹一下一下砸下来,炳恩说的字字铿锵,每个句子当中的间隔和词汇之间的喘息都拿捏的滴水不漏。他暗自演练过无数遍了吧,那些话他也修改过无数次了吧,他努力压抑着声音让这些话的杀伤力减到最小。他那些话背后有过深思熟虑,他想让她知道,这一次和他们此前无数次的小打小闹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他是真的要从他们的未来里,选择退出了。
雅宁都听懂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察言观色,这么些年过去,怎么能看不懂自己的男人。
可他没给她一个让她信服的理由,炳恩也知道她的沉默是在等这个理由。
她仰着头,不让眼泪鼻涕滴到婚纱上,背对着炳恩,后背剧烈颤抖得像个落了水的兔子。
炳恩的嘴唇嗫嚅的声音她都听到了,她知道他要开口了。
“雅宁你跑得太快了,我跟在后面有些累了。你的光芒总是那么耀眼,我怕被你比下去,这些年马不停蹄地朝前赶。你还想走得更高更远,我还是不要当你的负担了。”
“可我从没要求你变得和我一样啊。”雅宁的声音因为抑制哭泣变得沙哑。
“我不想和你有距离,那样会伤害感情。”
“已经伤害到没法复原了,不是么。”
换了离婚证回到北京,雅宁从家里搬出去了,走得悄无声息。她的东西收拾得干净利落,连一片化妆棉都没落下,甚至还用吸尘器吸干净了地板,她大把大把掉的头发丝也不着痕迹。
房间整洁的像是原本就是炳恩一个人的家。
她不纠缠,不哭闹。搬家师傅尴尬地问是搬一个人的东西还是两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她回答的干脆直接,就像她在北京无数次的搬家一样。反正在这里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家的,搬到哪里都是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在商场里争抢过来的,在情场里用心经营的,哪一样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让它一直跟着你。
零七网部分新闻及文章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若有涉及作者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删除或按规定办理。感谢所有提供资讯的网站,欢迎各类媒体与零七网进行文章共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