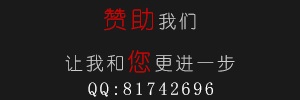我和她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
她从未像其他母亲一样慈善且宽厚地待过我,而我,亦不曾在任何时候为她献过一束芬芳馥郁的康乃馨。
高三那年,我恋爱了。每周两小时的上网时间已经无法满足我对骆小雪的思念,我开始在明月朗朗的夜晚给骆小雪写信,靠着窗,望着星空,一笔一画地书写着18岁的懵懂情怀。
因少时丧父的缘故,这些年我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但我从不把心里的悲喜和秘密告诉她,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在青春忧伤的年纪是否有过彷徨和莫名的沮丧。
和骆小雪认识之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终于收到了她的回信。掐指算来,短短3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给她邮去了40多封苦涩的密语。
我永远记得骆小雪站在松花江上的场景——漫天的大雪像鹅毛一般在天际下滚滚飞扬,一个蓄着乌黑长发的女孩儿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带着红色的帽子,系着红色的围巾,如同一团跳跃的火焰站在漫天的飞雪之中。
站在南方的窗台上,日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肩头。我伏在栏杆上,微弱的呼吸就像骆小雪身后的松花江一般被冻结了。
为了能把这段青涩的恋情延续,高考结束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填下了3所东北城市大学的代码,将那些曾经对母亲说过的、绝对不会离她500里的承诺抛诸脑后。
临行那天,母亲赶来送我,57个小时的辗转,几千里路的奔驰,使她左右放心不下。那是她第一次跟我说那么多话。她说,幼时就听父辈们讲过,黑龙江在中国的最北端,不论冬夏都冷得难以忍受,叫我去那边之后无论如何也得买几件厚实的棉衣。
站在南国的小站上,我忽然内心一片汪洋。我这一走,她又要再次陷入一个人的孤独。但我始终没有说出心中的关切,而她,亦没有坦白她的不安和不舍。
我俩就这么僵持在寒风呼啸的站台上,等待火车鸣笛。我努力擦着雾气腾腾的车窗,可还是看不清她故作从容的背影。
由于火车晚点,原本57个小时的行程竟然拉长了几个钟头。我躺在动荡的卧铺上,胃里翻江倒海。她明知我会晕车,却一个电话也不打来。
我以为我会在阳光明媚的松花江上见到骆小雪,却不料她竟做了一个与我相反的抉择。恋情和人生,我选择了前者;而她,却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后者。
一千多公里的距离,终于使这段几经波折的萌动情怀在流动的岁月里无疾而终。我给骆小雪写了很多信,却不知该邮到哪里。
失恋之后,我忽然讨厌这个夏热冬冷的无情城市。校园里到处都是十指紧扣的情侣和粗壮的法国梧桐,它们像无孔不入的细菌,啃噬着我的伤口。
冬天的时候,我跟团去了松花江。在南国长大的我,第一次见到结冰的河。我沿着河岸一路狂奔,而后气喘吁吁地脱掉笨重的外套,站在骆小雪曾经留影的地方照了一张快相。
我原本想把这张照片送给骆小雪,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瞻前顾后,最终还是把这张洒着漫天雪花的照片邮给了远在南国小镇的母亲。
她一直没有给我电话。我以为,那封穿越千山的平信早已丢失,却在半月后收到了一包颜色各异的棉服。
大学第二年,我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正当我沮丧且无助时,她竟以下岗无业为由,扣发每月对我定时支付的生活费,逼迫我在校勤工俭学。
无奈之下,我只好辞去一切琐碎职务,一面帮私企写广告软文,一面在校外的超市当搬运工。不管我如何心力交瘁,她都从不会问我生活是否困难。因为她的冷漠和决绝,我们的母子关系日渐恶化。大学毕业那年,我依然选择留在外省打拼。
年前回家,叔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小海,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真高兴。你妈当初还一直害怕,自己的良苦用心会使你走上另外一条错误的路。”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再次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模样,才恍然明白她内心的恐惧和渴盼。1400多个日子,她必须时刻忍住母性本有的挂念,狠心将我抛在未知的世界,而后不闻不问、夜夜忐忑。
因为爱我,她才有这些无处可躲的悲伤。
零七网部分新闻及文章转载自互联网,供读者交流和学习,若有涉及作者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更正、删除或按规定办理。感谢所有提供资讯的网站,欢迎各类媒体与零七网进行文章共享合作。